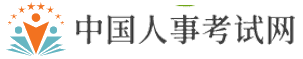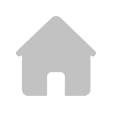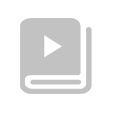大家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概念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可以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譬如,有人溺水,你为救他而捐躯,或与一个抢了其他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个时候,大家非常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非常难考虑到假如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功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大家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看法:市场经济没必要谈道德,持这种看法的人主如果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总是强调要道德做什么,有市场经济已经足够,市场经济会在角逐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程度突出到如此的高度,就是说,可以将道德概念成:但凡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须是考虑功用函数很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会处于非理性范围内。大家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大家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是否有必要,道德是不是是一个买卖的结果,是个充分角逐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买卖如此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样为何还会有如此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不是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无需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含对产权的尊重、对别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假如用我对道德事件的概念,那样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括在这个定义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是为我们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假如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只是自私的一群人,那样所有些别的人都只不过他们的方法,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方法。其他人是我的方法,同样你也是其他人的方法,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别人的方法。在如此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能不能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非常明确的:不可能。在大家熟知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成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看法:即使是一群自利的人,假如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觉得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状况。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类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 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一个人都需要尊重别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些尊重与英美传统有非常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须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大家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年代之前的时期,并不看上去非常重要,由于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无人认识到它一旦缺少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形成启蒙年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怎么看: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机械式的同一。由于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非常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很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非常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常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 solidarity ,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大家面临同样的存活问题,大家拥有几乎同样的存活方法,也就是大家拥有同样的功用函数,那样大家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类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进步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pvidualism)的进步。由于分工将来,大家的常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大家在具体环境中积累常识,那样每一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常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比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状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非常随便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打造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买卖、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靠、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大家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规范,是非道德的,由于它不是依靠于一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靠分工规范,就像将每一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一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觉得是社会主义者,由于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打造,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有哪些用途。他企图如此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况。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如果欧陆哲学家。包含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根据哈贝玛斯的看法,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打造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大家还想不出有思想家比如启蒙年代的洛克、休谟、斯密如此的人,在要紧的文章,要紧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由于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发生与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完善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 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 court)而形成一种很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 law),来解决平时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 by case 。法官遇见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案例,假如没就按我们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大家对现实问题的讲解和处置非常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进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可以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方法。
大家中国人基本就受这两方面西学的影响。要么就沿着英美的思路,提出一些合适中国的问题或中国式的问题;要么就遭到欧陆哲学的影响,包含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所谓中国式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关心的是中国、立足于中国的前途、中国的命,考虑的是中国人所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问题意识是中国的。像国有企业改革、农业进步问题、关贸问题等等一些非常细致的现实问题。当与一个外国人讨论时,假如他不了解提出问题的背景,你提出一个学理性问题,他就会照本宣科地对你说,这个定义是什么问题,像公民权利的意思是,法制的意思是,但他不会涉及中国的问题。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问题意识只能是当地的。目前不是每个人都是有问题意识的,在很多学者提出一个政策或一个理论中完全看不到问题意识。当然,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是没这种问题意识,而只不过隔靴搔痒。假如有了这种问题意识,并在这里面提出正确问题,在求解时再参照一些其他社会、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经验,回到西方去看(由于不少学问都是西学)时,就会出现几种倾向,一部分人就到欧陆哲学中去找一个适合的参照系、一个启发,经过启发后回来独立地求解中国式的问题;另一部分人是从英美传统中去探寻启发;还有一些学术练习比较全方位的人综合考虑两方面的传统,同时还有问题意识,这三者兼得是困难的。
在此大家强调的是作为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基础的道德共识,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两个源流对大家中国人处置问题有不一样的影响。当大家处置道德共识问题的时候,大家不能不处置什么是自由这个定义。在欧陆传统里,卢梭有一个怎么看:田园诗式的野蛮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充分自由的。由于那时候人少地多,从树上摘果子就可以吃,也就是完全没资源稀缺性,没对于稀缺资源的角逐关系,所以那时或许是很美好的,像田园诗式的浪漫的,在这种标准下,每一个人是很很自由的,他不必考虑其他其他人与他的角逐关系。卢梭当然非常羡慕那时候的人,霍布斯也很羡慕这类野蛮人,这种田园诗式的野蛮生活。但因为经济学家看到的资源稀缺和对稀缺资源的角逐,产生了残酷的以别人作为方法的存活方法,这个时候人就开始不自由了,那样每个追求自己充分自由的人,假如对自由无限地需要下去,必然会逻辑地把别的人作为自己存活的方法。在欧陆,在法国传统里就是充分的个人自由,在德国从康德的要意志(will)的自由,进步到黑格尔极端的状况,中经谢林、费希特的思想。总之,欧陆传统中提出了像伯林讲的两种关于自由的态度。这里用态度(attitude)而不需要立场,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每一个人都觉得自由是好事,可对自由的程度每一个人的认识并不同,你可以追求非常大程度的自由,以致追求到你觉得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你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假如你追求的个人自由那样广泛,那样彻底,以致你的主观意志、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体现出来后,结果就是你控制了别的人,你把所有些人都作为达到你的个人意志的方法,解放你一个人的一个方法,这就非常可怕了,这就是希特勒的集权。我所倡导的自由,是所谓消极的自由态度,就是你站在自由两个极端的中点上,在如此一个适可而止的,止于至善的点上,你向左侧望就是积极自由,你就很地想控制其他人,你向右侧看,你就抱着一种消极的自由态度。所以这是一种态度,大多数人立场都是差不多,没多少人是希特勒,大多数人更不是完全不要个人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态度区别,态度区别尤为重要。假如处置不好就会致使 “文革”悲剧或法西斯专制。处置得好就会出现市民社会或社区生活。这都是从两种态度的差别生发出来的。所以我强调先在态度上讨论。两种自由态度就是伯林的名言,一个是free to,你做事情的自由,一个是free from ,我防止事情的自由,我不想去干扰其他人,同时我也从控制中防止出来。追求这种自由的人必然会承认他对其他人同等的消极自由的责任,也就是在自由中间没绝对的自由,这里有个度的问题,那样为了保持这个自由的度,你将对别的人的自由负担你的义务,你只有如此按基本的对等原则(道德黄金律)做才可以有你的自由。不然大家之间就是野蛮的、互相杀戳的关系。所以消极的自由态度包括着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你的隐私、小天地(privacy),其他人不来干预你,另一面是其他人不来干预你的义务,是社会所有人达到的一种道德共识,譬如像觉得不应该闯入其他人家拿了东西就去卖等等。所以,你在享受其他人不干涉你的权利的时候,也担负着尊重其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这是一个辩证统一关系。大家谈的自由就是如此的自由,而不是单向的自由,不是积极的自由。所以大家可以说,为了确保最大限度的这种消极自由,大家迫不能以,非要加入如此一个文明社会,在这种社会,每个人都承担着对如此的自由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是洛克说的产权。这就是在大家这个传统中所说的道德共识。就是每一个人在宪法上都签约:我作为中国公民赞同尊重其他所有公民的生命、基本自由、基本财产占有些权利。在这个根本宪法的签约之下,你才谈得上立法过程、执法政府,由于抽象的宪法不可以解决各种具体的日常问题。所以你要立法,要有符合宪法的政府。总之,这一套是是政治哲学的内容。这一套之前是是道德哲学的内容,只有在这两套体系之后,大家才能谈到所谓经济生活,经济生活才有一个规矩,才有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社会的结构——每一个人都在服从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任别的人也在他一个人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样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假如大家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如何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一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大家发现都有如此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一样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非常大,但都有如此的思想。由于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现在所存活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一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别人,由于他会理性地判断假如如此做,其他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由于,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备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致使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的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大家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已经足够。假如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非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假如大家将它放到日常考虑,大家每天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大家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源于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非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平时生活烦恼不能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样怎么样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常见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如此:第一,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譬如是不是说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此时此刻,假如你觉得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样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否你一个人在所有些场所,所有些状况下都要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假如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否所有些人在所有些场所、所有些状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若是,那样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常见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不少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譬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个时候只有你了解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说谎还是不说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由于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怎么看就是,真的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常见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常见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起来“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目前不少的道德研究都觉得,仅仅靠常见主义推出来的原则,能不能推出指导大家平时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可以。这就像宪法并不可以处置大家日常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置大家日常遇见的麻烦、冲突,还不可以仅仅依赖一些最常见的道德准则,大家还要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大家中国的文化来讲,除去孔子对仁的怎么看具备常见主义外,后来是愈加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一直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常见主义,是大家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喜欢的是爸爸妈妈,第三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别的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大家中国的实质状况。
面对大家今天现实日常道德滑坡的局面,在大家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讲解现实时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大家的剖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感觉,就是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了解,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爸爸妈妈、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类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非常深切的理解,断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哪种关系,然后根据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置各种关系,去与其他人博弈,一直处置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如此行为。譬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样爸爸有罪,儿子包庇,这里包括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可以,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如何处置,而不是事实上如何处置(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可能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事实上不少事情你不能不做,但你觉得不道德,你觉得可能不对。这是每个人都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冲突,每一个人一直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无法,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紧急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因为大家缺少强有力的常见主义原则,那样如何才能形成道德共识?比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将来,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非常有共识的。而目前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有了利益冲突,就面临启蒙年代大家所遇见的道德危机,原来的共识就开始崩溃,就开始“杀熟”,越好的朋友越宰你一刀,由于他没方法不如此行事,由于这是在特殊主义原则指导下。结果有不少在乡土中国条件下可以达成的道德共识这个时候就达不成了。像义利之辩影响就非常大,比如反暴利法的产生,就有一个文化背景,有一个传统。
所以对于大家如此一个本来就缺少常见主义原则的社会,一旦走入市场经济或现代的分工社会,那样原来赖以维系社会的家庭联系就被冲烂了,血缘关系就被淡化了,那样与血缘关系联系的前现代化的共识就瓦解了。而宗教生活大家又没,没一个从中世纪带来的遗产,就是把上帝变成法就完事,使社会有一个自然秩序的条件。所以就变成了任性妄为的状况,大家就开始追求最眼前的利益——货币,用钱来指导人的行为。这个时候你没道德准则了,你从小到大,无人对你说什么行为是道德的,道德是教育出来的,是一点点在传统中熏陶出来的,可大家的传统正在巨变,正遭到冲击,每个人都开始失落。假如按正常的状况,即使在一个特殊主义社会,也先有一个道德的基准,在这个参照系之下,大家了解向道德方向去努力,就是文明化的过程(civilization),而目前大家好像不是如此,而是有点野蛮化过程,由于,无人去指导,大家完全是看如何自私就如何来了。大家只不过靠理性驱动,他的利益函数、功用函数,力求在现在最大化,以后的事也不想了。严格地讲,大家社会日常的事是要经过多次博弈的,就是说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应该考虑到无穷远的将来的收益,然后将它折现到目前使功用最大化,这个最大化就大概是道德性的行为,也就是顾及别人的行为,由于假如毁掉了名誉,将来就无法与人合作。但大家处在过渡时期,将来贴现值不确定,以致无人考虑。结果每个人都愈加短视,所以就会看到大家社会现在的假冒伪劣,这都是不要将来名誉的行为,一个规范的社是否会有这种现象。这又形成劣币淘汰良币,假如你顾及名誉,你就吃亏,以致存活不下去。结果就非常危险了。一旦出现了这种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影响破坏了互相信赖的关系,假如这种道德风险代价太高,没一个机制来平滑它,那就是逆淘汰,是劣币驱逐良币,那样最后这个社会里都是坏人,那些稍微好点的人都生活不下去。我总举这个例子,就是人类学家(Ruth Benepct)察看到的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以能骗住所有些人为英雄人物的规范,就是大伙都服骗术最高的人。大家可以设想,假如一直坚持这种标准,那就没贸易、交换、信赖可言,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崩溃了,结果这个部落几十年将来就会自然消失。
在现在的时刻,我并非雷锋,我也不想让每个人来考虑道德问题,但我感觉道德的危机就在大家身边,假如大家处置不好,那无论是改革还是市场社会的进步都非常困难了。
非常可惜,对现在的情况,我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法。我在香港除去规范经济学,就一直都是研究企业家行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规范革新是企业家的行为而不是理论家的行为。那样哪种规范可以使大家的道德危机得到缓解,我不了解,我只不过说这是一个企业家革新的过程。我总用如此的例子,就是在最大的企业之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盗对强盗的规则,就是说,假如你不守规则,那你就去世了。所以在这一层次的企业家名誉尤为重要,他们开始向长远着眼, 不是搞短平快。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是有道理的。因此,有充分的角逐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秩序。但这个秩序是不是可以扩展,扩展到中小微型企业,那还要察看,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是一种期望。从理论上可以提出来的一个原则(不是规则),就是角逐性原则。大家并不了解什么是真的好的规范,但我了解真的好的规范肯定是角逐的产物,是规范革新,是各种不同规范之间角逐产生出来的结果。这个角逐的结果可能是没一个人认可,但这是大家得到的最好的规范或最不坏的规范。所以,只有充分角逐才是大家得到好的规范,解决道德危机的唯一渠道。这就回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阵营,只须允许大家自由交往,或许就能打造规范及道德共识。
但,现代经济学还不现代,由于它没考虑人存在的意义这个现代问题,或上面大家说的现代危机这个问题,大家声称现代只是数学用多了点。因此,为了使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需要第一回到古典,处置古典的问题。由于古典经济学的年代正是启蒙年代,正是那时候大家认识了现代危机。所以大家要回到古典经济学,重新梳理出现代传统,这才能继续往前走,进入现代。假如缺少这种眼光,就值得批判。我一直在考虑现代经济学,我是从存在哲学、从存活论的角度来从新写经济剖析。事实上大家做的任何一项经济剖析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大家的价值判断最基本的就是从存活哲学、从存活论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对大家有哪些意义这个角度,来给出大家的价值判断。在这个判断基础上,才可能有类似功用函数,博弈均衡的选择这类能动的选择,去改变传统、去改变均衡、去进行规范革新,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才现代化了。就是把人的意义考虑进去,而不是像新古典的现代经济学所表现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东西来控制。现代经济学无非做得动态化一些,像最佳控制理论,但大家只须问人在哪儿的问题,就会发现目前经济学的缺点。我想中国人假如说可以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可以继承它并超越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大家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由于在中国哲学中的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中来,这就大概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点的经济学。
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的现代化
点击数:911 | 发布时间:2025-06-18 | 来源:www.ewonz.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国家人事考试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国家人事考试网(https://www.scxhcf.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国家人事考试网微博
-

国家人事考试网